今年年初,国家药监局发布 2020 年第一号文件——《真实世界证据支持药物研发与审评的指导原则(试行)》,在业界引起高度关注。两年前,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,在《樊代明院士:过于关注微观,医学或将走偏》报道中,樊代明力推“真实世界研究”,呼吁开展医学的反向研究。
现在,樊代明依旧忙碌,对医学发展的思考也不断深入:为何现代医学越发展,受到的质疑反而越激烈?文化之于医学,究竟是什么关系?如何重塑医学文化……不久前,樊代明再次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专访,他郑重提出——以文化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方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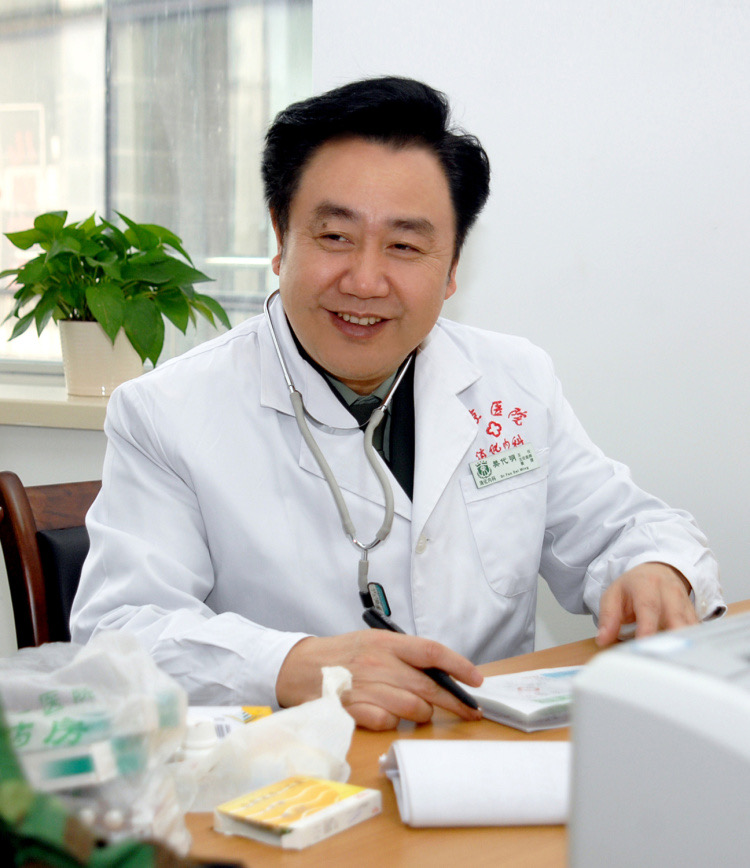
樊代明
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副主席,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
樊代明:
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窘境——现代医学使人类平均寿命极大提高,但是医学受到的质疑,也从未像今天这么激烈。
正如剑桥大学医学史教授罗伊·波特所写:
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,活得这么健康,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,然而矛盾的是,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,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。
事实上,现代医学发展出现了四个偏向:
一是医学研究一味地向技术发展,一味地向微观渗透,导致了专业过度分化,专科过度细划,医学知识碎片化即 O2F1;
二是现代医学变成了等待医学;
三是现代医学变成了对抗医学;
四是医学异化,把生命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身体的某些自然变化,都当成疾病进行过度干预。
记者:关于 O2F1,此前您在接受我们采访时,曾有过详细阐述。
樊代明:
是的。这个状况至少是把简单的研究方法引入医学所造成的问题,即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引入到复杂的、可变的人体健康医疗中,医生越来越局限在狭窄的专业领域,甚至只能看某一种病,导致药越来越多,但疗效却越来越差。我重点讲后三个偏向。
现代医学成了等待医学。现代医学将人的健康状态,从没有病到因病死亡,看作一个线性的过程。什么叫病?就是根据某些指标人为地划一条线,等你越过这条线就是生病了,医生就给你治;没越过这条线,医生就不管。
以脑卒中为例。
一个人没发生脑卒中时就是一个“好”人,某一天突然卒中就成了病人。
脑卒中发病后,治疗几乎发挥不了太多作用,但病人一辈子挣的钱,却很可能在最后这几天给用完了。
只在疾病末期、生命最后几天发力,疗效必然有限,还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,这就是等待医学。
假如说我们在“病”之前多下一些功夫,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?
中医提倡的“治未病”,应能给现代医学足够的启示。
现代医学成了对抗医学。
过去,外来、单一病因导致的传染病是人类健康最大威胁,把病都当成“敌人”来“对抗”,无可厚非。
但在当今,慢性病已成人类健康最大威胁,这是人自己身体内部平衡调节出了问题,如果还采用“对抗”的思维,就是在“对抗”自己,可能治不好“病”反而伤及其他器官。
这种“对抗”思维,也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。
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医学源自游牧文化,游牧文化生存法则是“你死我活”;
而在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社会为背景的传统文化中, “和谐” “你活我也活”是主流,所以中医治癌症,是“治瘤不见瘤”,是如何更好地“带癌生存”。
医学出现了异化。
把生命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身体的某些自然变化,都当成疾病进行过度干预,这种做法严重过头了。
比如,妈妈生宝宝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如果在怀孕过程中有点问题,偶尔去检查一下是可以的,但现在好多孕妇每一两个月都去做B超检查。
要知道,每一次医学检查对人或多或少都有损伤,只是这种损伤在可容忍的范围内。
但有人想过吗,经常性的产检,对胎儿的远期伤害究竟有多大?
多年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?
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
记者:医学发展与文化关系的失衡,或者说医学发展中文化的缺失,会给医学带来什么?
樊代明:
至少有三方面的后果。第一,在科技的帮助下,医学对人体结构乃至功能的研究已经很先进、很透彻,直达基因,但医学从文化上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还差得很远,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要知道,生病不只是身体得了病,更是生命得了病。医学发展与文化关系的失衡,或者说文化医学的缺失,使现代医学有些“魂不附体”。
第二,在世界范围内,人类文化(包括医学文化)已形成发展了几千年(比如欧洲文化、印度文化、中国文化),但我们现在是用只有几百年的单域文化(比如医学伦理文化),去统揽甚至取代几千年的全球人类文化,从而显得有些“力不从心”。
第三,和以前相比,当代人类的疾病谱已发生了根本变化,如各种内生性的老年病、慢性病,多病因多靶点;
而在历史上,人类寿命从未像现在这么长,对健康的最大威胁往往是体外因素导致的、单病因的传染病。
现代医学还在用简单的、线性的、直接的、在体外形成的应对传染病的方法,去处理人类现在复杂、非线性、间接的、体内自生的慢性疾病,所以常常“事与愿违”。
从魂不附体,到力不从心,再到事与愿违,这样的医学文化不改行吗?
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重塑医学文化。
医学究竟向何方发展,取决于什么样的医学文化来引领。
记者:有人说,科技与人文,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个翅膀,缺一不可,否则就会偏离方向。看来,对于人类健康而言,医学与文化,也是如此。
樊代明:
医学与文化关系处理不好,不仅不利于患者,对医生同样会造成伤害。在追悼会上,通常会说“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去世”,却不会说“因病去世”。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,严重的伤者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,在通报的时候会说“因伤抢救无效死亡”,却不会说“因伤重死亡”。还有,“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”,这从人道主义是对的,但在医学实践中这完全对吗?这对有些病人是劳民伤财,对医生是劳而无功,对社会是得不偿失。
“医治无效”“抢救无效”“医学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”这样已成“惯例”的话,对医生而言,何尝不是一种过度的指责与伤害?这也是文化出了问题!
伤害医生的案件层出不穷,则是更为极端的现象。
让伤害医生的人受到应有惩罚,甚至是判处死刑,这样问题就根本和完全解决了吗?
不!
一定要从医学与文化、价值观这个根源上思考,我们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。
记者:在您看来,处理好医学与文化的关系,应当包含哪些内容?
樊代明:
人文是文化在人性研究中的最高境界,其功能是保障生命的安全、生命的重要性和尊严。人性最基本要求有两个:一是追求幸福,一是追求不朽,希望长生不老。事实上生物体要不朽是不可能的。人也一样,花开花落,潮起潮落,万事万物,无不如此,这是自然之中的必然。
但问题在于,现在单域的医学伦理文化并不承认人会寿终正寝,于是用技术去干预死亡。
于是就出现三个问题:
一是死亡时间从未知变为已知。
二是死亡的地点从家里搬到了病房。
我们过去是拿药回家养病,现在是直接把病人送到医院救死,即使知道希望不大也要尽力抢救。
ICU 里、抢救室里医生使劲抢救,外面家属使劲交钱。
很可能最后病人走的时候,家属都没能握手告别。
三是从自然死亡到了技术死亡。
我院一位老专家在他 92岁的时候离开了,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他成了植物人,灵魂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,我们还在他身体上猛下功夫,依靠呼吸机维持。
这样的人很多,虽躺在病床上却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他们满身插满管子却毫不自知,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可言。
医生在看管子通不通,全通就是活,不通就是不活,部分通就是部分活。
这对吗?
这种文化不改行吗?
过去,中西方的祭祀习俗都充分考虑了生命的神圣和尊严。
时下很多医
院专门开设的安宁医护,充分考虑到家属的情感和医护人员对亡者的临终关怀,事实上这也是对医学文化的一种重塑。
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。
生命是以整体存在的,随着无限的破分,最后所有的局部都存在,可是丢掉的是生命。
反过来,所有的局部加起来并不等于一个整体,因为医学的整体一定要有生命。
有生命的整体,我们才叫整体;
没有生命的整体,我们叫尸体。
生命的存在,一定是依托整体存在而存在。
一头大象,我们一看就知道了,盲人只能靠触摸。
当盲人摸到象腿时,他能分辨出这是大象,但如果摸到细胞甚至分子,还能认出是大象么?
如果再到原子、量子层面,万物已无区别,还能识别出生命形态吗?
所以,医学不能太微观。
爱因斯坦早就说过,科学追求明晰性、精准性和纯粹性,是以牺牲完整性为代价的。
同样,在医学上我们一味追求的“精准”,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,这也是文化,是出了问题的文化。
生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,局部、瞬时的研究结果,不能解释生命的过程和本质,也不可能成为拯救生命的良方妙药。
我们现在认识生命,太简单了,其实它极其复杂。
生命的存在,首先是有自然力作用的。
否则,在没有医学的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里,生命是如何度过的?
这种自然力,一表现为生命本身具有的抗病抗害能力;
二是不同的器官能相互协调有自洽能力;
三是体内的某一部分损坏后可以补偿生长,具有自我修复能力;
四是新陈代谢能力,生命体能与外界交融,吸收有序能排出无序能;
五是自我平衡能力,比如水和电解质平衡、白细胞高低的平衡、热的平衡等等;
六是自我保护能力,这种保护能力表现为免疫力,还表现为吃了坏东西会呕吐、排泄等;
七是精神、意识对上述六种能力的反作用。
有一种说法,医生治疗疾病的“三大法宝”是用语言、药品、手术刀。
其中,药品、手术刀是不得已而为之,语言的力量是最大的。
西方有一句名言,“To cure sometimes,To relieve often,To comfort always”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,对病人而言,舒缓和安慰是最重要的,治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。
其实,即使病人治愈了,归根到底也是病人自身内在的自然力发挥了作用,医生只是在外部帮助了他们而已,绝对不要贪天功为己功。
因此,医学对生命健康的干预,应首先保证生命自然力发挥作用。
如果医学的干预超过了这种能力限度,甚至取代这种能力,就叫过度医疗。
从现代医学的发展实践看,医疗不足的事情越来越少,医疗过度反而越来越多。
现在很多医学研究是不真实的,只是一条路单向走到底,从宏观到微观,或者从结构到小结构,从长时间到短时间。
一定要再走回来,重新回到宏观的层面,就是我们说的反向医学研究,只有回来的路走通了,形成一个圆圈,叫闭环式的研究,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。
历史上,自然科学,特别是医学,很多巨大成就都是反向研究而获得的。
医学研究要改变现有临床思维,要完善循证医学的不足之处,根本的方法就是反向思维。
反向思维涉及多个方面,其中包括真实世界研究。
真实世界研究可能也有自身的问题,如果循证医学再加上真实世界研究,特别是在循证医学上加上反向研究,我们得到正确结果的可能性会大得多。
当然,四个坚持是重塑医学文化的必要条件,只满足于这四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。
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进来,共同为重塑医学文化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。
樊代明:
有人说,要解决当今诸多全球性问题,应回到 2500 年前的古代中国,学习孔子的智慧。孔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,那时有“三教九流”“诸子百家”,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,前看 2500 年,后想 2500 年,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树立了今人难以企及的思想丰碑。
那么,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化精髓在哪里?
我以为,是以人为本的整体观、天人合一的整合观。
整体整合医学的根源、思想脉络就是从这里来的。
而在医学文化重塑上,中医整体论和西医还原论有机整合,应是不二法门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世界万物分阴阳五行,阴阳互根,五行相生相克。
在此基础上,中医提出“精气神”,精是物质,用现代医学手段可以查出,如血红蛋白、血脂等,气和神仪器查不出来,但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可感知其状态水平。
这就是结构与功能共同的表现,是古代中医对医学的认识。
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,中医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疗效,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远超出了现代医学的认知水平和疗效,值得现代医学虚心学习、借鉴。
在中医发展历史中,道家、佛家、儒家贡献良多,现代医学文化的重建,能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。
如,佛家讲修心,强调一个“净”字,要求心无杂念。
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
心中总是有很多杂念,能健康吗?
如果天天想如何算计别人,能健康吗?
又如,道家讲养生,强调一个“静”字。
心态总是比较狂躁,能静下来养心养生么?
所以要做到处变不惊,才能保证健康。
再如,儒家讲治国、经世济民,强调一个“敬”字,要做到敬畏自然,敬畏社会,敬畏礼法。
科学本身没有目的,用好了可以造福人类,如核电技术;
用得不好同样可用之杀人如核武器。
用得好与不好,需要文化来引领。
对于医学而言,亦是如此。
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,其整体论、整合观与西医的还原论加以整合,将形成新的医学文化,只有形成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,其中包括整合型的医学教育体系、医学研究体系、医疗服务体系、医学预防体系和医学管理体系等,只有这样,才能引领医学发展的新方向,才能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、呵护人类健康的事业中走得更快、走得更远,关键是走得更好。
【编者注】这是本报连续四年对樊院士的采访——2017年《“西医院士”樊代明:
我为何力挺中医》,2018年《樊代明院士:
过于关注微观,医学或将走偏》,2019年《三访樊代明院士:
现代医学需要“反向研究”》,2020年则是本篇,主题为“医学发展与医学文化”。
关于未来需要构建的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,樊院士已思考很多,抗疫期间他写过一篇5万字的大作《试论医学的正确实践》,分四期在《医学争鸣》上发表,明年(第五年)的专访或许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。
(记者 王小波 王奇 北京报道)
